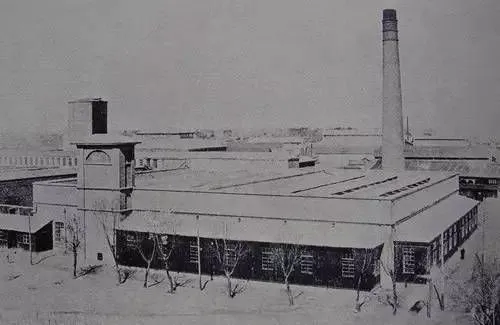孙钦香|张謇“实业儒学”思想述评发表时间:2024-08-20 08:38来源:《学海》2024年第4期 就今日中文学界而言,对现代性(或启蒙)的反思蔚为大观,但必须指出的是,反思、批判现代性绝不是推倒一切现代文明(物质和精神文明),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过重新回溯、诠释不同文明的传统思想资源,为现代社会提供和培植一个更宽广、更多元的思想文化土壤,以消解现代原子式个体主义、虚无主义等意识形态对意义世界理解的遮蔽。换言之,在古今中西问题上,既要反对那种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又要避免极端保守论者“盲目信古”的偏向。 本文不以明清之际商人阶层的兴起为例,而以清末民初张謇这位近代民族实业家为例。在笔者看来,后者更能准确地回应韦伯的疑问,即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也更能有效地回应儒家伦理是否如韦伯所言不能为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 理由有二:第一,清末民初近代实业的兴起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即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经济生活形式;第二,作为近代民族实业家的典范人物,张謇秉持儒家伦理精神以兴办实业,其“兴实业”由明清之际“求实用”“明体达用”等“实学”思想演变而来,是儒学内部一条通往近代机器工业的思想与实践路径。 概言之,相比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兴起的商人精神,这种源自关注天文、地质、经济诸事的明清之际的实学精神,无疑是清末民初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思想根源之一。
“国以农工为本” 虽然近来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传统治生、谋食、制产等问题,但不可否认,传统儒家思想仍以“谋道不谋利”为主流,即便明末清初“士”“商”合流,也只是暗流;而传统的义利之辨、农工商本末之辨等问题发生根本的思想变化,却发生在清末民初。承担这一思想观念革故鼎新之使命的主体是近代民族实业家,其中张謇是传统士大夫与近代实业相结合的代表人物,是“实业儒学”的典范人物。 张謇身为清末状元、翰林院修撰,走的是传统的士人读书出仕之路,熟读经书、研习经义策问之文,是其日常之务。其在《柳西草堂日记》中常记载“读文”“作文”“写字”等事,自述从“5岁到7岁,读《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孝经》《学》《庸》《论》《孟》毕”,13岁读完《论》《孟》《诗》《书》《易》等,14岁读《礼》《春秋左传》,且作诗并“制艺成篇”,15岁读《周礼》《仪礼》,20岁读《通鉴》,21岁读《三国志》,22岁读《晋书》等。但因时代风云际会,此一传统道路却不得不发生折转。 1894年,张謇中状元,不久丁父忧,赋闲在家,对张之洞举荐、委派他在家乡通州兴办纱厂一事,甚为赞许,他回复张之洞曰:“公所请借洋债千万,分办丝纱厂,合官绅商民之力通筹抵制,甚盛意也。”对此因缘际会,张謇曾多次谈起。1913年,他自言:“鄙人自前清成进士后,默察世界之大势,谛观内政之状况,知时局不可与有为,即绝意仕途,愿为社会稍效微力”,又“深信非振兴实业,不足以利用厚生而正民德”。 于是“自脱离科举后,投身实业界,适当中国否塞之时”,面对如此时局,张謇在提出编练陆军、亟治海军、广开学堂外,还强调“速讲商务”和“讲求工政”。张謇借助对先秦儒家经典的解读,对后世迂儒“末务”之见提出批评。当然,这不是说张謇对农业不予重视,他指出:“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可见,就农工商三者的关系而言,张謇虽认为“农为本”,所谓“天下之大本在农”,但也不轻视商,认为“今日之先务在商”,这是因为“不商,则农无输产之功”。概言之,在张謇看来,“商农者,生民治命,国计之原,以其本末相资而为用者”。 张謇重视农工商,虽分本末,但并不偏废,认为:“实业之曰农、曰工、曰商者”,是人类之“不可或缺者”,因为“人民之生活本此,即教育之目的在此”,即以一国之大势而筹划,则“赖农而生者十之五,赖工而生者十之三,赖商而生者十之二”。张謇强调兴实业与国家富强密切相关,所谓“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呼吁致力于“农工商”,认为“士竞学,农、工、商竞业,而天下乃无不大之族,无不昌之国”。简言之,农工商兼重,便是张謇所谓的“实业”,即“实业赅古农、工、商、矿,今声、光、电、化,事有越于《周礼》地官、冬官之外者”。 他指出:“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而就传统论题中“本对末而言”,张謇给出的解释是“犹言原委,义有先后而无轻重”。这是说,传统的“农本商末”其意是原则上有“先后”之序,但却没有轻重之分。而且《尚书大传》舜“贩于顿丘,就时负夏”以及《史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中所谓的“就时”,便是“若乘时射利也”。 这是说,舜“无论耕渔之为农,陶与作器之为工,就时之为商”,确有其事,如果舜只是作自了汉,但舜二年成邑,可见舜之“实业发达”,如若不是,“亦未必人人归附如此”。可见,与传统思孟学派、程朱道学所刻画的舜之形象不同,张謇突出舜之耕作、捕鱼、制陶、营商等农工商事业。前者更为强调舜作为大孝子的面向,而在张謇笔下,舜的形象则是实业政治家。 在张謇看来,中国古代的圣人并非宋儒所论之形象。他指出:“中国讲哲学之最古者,莫如《易经》,其次则《礼记》亦有所发明。《易》《礼》讲圣字,圣即无所不通之谓,宋儒解释拘束,失其本义”。可见,与宋儒偏重从内圣德行的角度描述圣人不同,张謇对于古代圣人的刻画侧重在“平水土,教稼穑”。他指出:“中国古圣人之功,莫大于平水土,教稼穑”,而且“必水土平而后稼穑兴,必稼穑兴而后衣食足”。 而就《论语》中樊迟之问稼问圃,张謇也给出一个新颖的解读。首先,他指出,樊迟所问并非“农之学”,即不是农业知识,而是“学治农业”,对此,孔子自然承认在从事实际农业方面其不如农圃。因为“业非素习不能为”,孔子未尝学习农圃之业,因此不如老农,不如老圃。可见,孔子之言“非欺人之言,亦无疾怒之意”。而所谓农圃为小人之事,张謇认为“小人对大人言之”,就如现在所言“人民对政府”,有老农、老圃在,士大夫自然不必俱为老农、老圃,但这并不是说“天下不须稼”。如果真的不须稼穑,就能成就礼、义、信之天下,那么诗书所载,尽可以删除,为什么还要“留豳之诗”?而且古代农民,也不是一点学问没有,如《周礼》“骍刚用牛,赤缇用羊”等“定物地土化者”如此详细,再如《诗·大雅》“黍稷重稑,禾麻菽麦”等“言农种农具者”也如此详备。 于是,张謇批评“今使人学不足以治一生,而侈谈大用,疏矣”,提出“服田力穑,身不可为惰民;谈道读书,志必须为名世”,而且稼穑与读书“本是贯通”。他认为樊迟也不是小人,其用意是“用稼于世”,提倡“尚德而慨躬稼之劳”;而孔子对樊迟的回答是从“农之政”角度立言,认为“政盖尤有其大本”,此大本便是“礼义信”。具体而言,张謇认为,“上好礼义信,则与民相见以诚,相浃以分,有以立乎商政、农政之先”,如果是没有礼义信的君主,而言通商、劝农,则农民又如何能够勤业乐群? 综上而言,在农工商本末关系问题上,张謇对中国“尊士卑商,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此说“餍乎人心,千百年来,凡百营业,听其自生自灭,从未有提倡而保全之者”。此说在闭关锁国的时代犹可行,但“处廿世纪商战激烈时代”,那必然是“在天演淘汰之列”。由此,他提倡国家设立商部,民间成立商会。“中国之贫,全在各种实业未尽兴办,如在兴办之后,吾国何至于贫?”清末民初,由批评传统的重农抑商之见到追求富强、创办各种实业渐成潮流,张謇无疑是其中的代表者。他自言:“余从事于实业一途已阅半世,今则愈知欲富强吾国,舍实业无由也”,自称“半生精力耗于实业”,一生创办了数十家企业。 “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 就传统的义利之辨而言,张謇将其限定在为官领域,他指出:“居官,安有致富之理?”古代虽有为贫而仕之说,但也只是从事颇为低等的职位,如“抱关击柝”之类;而且“自一命以上,皆不当皇皇然谋财利”。可见,张謇认为为官与谋财是不可兼备的,特别是官阶大的更不应该谋求个人财利。“据正义言之”,皇皇以谋财利为目的的,“惟有实业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张謇之所以创办这么多企业,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谋个人之私利。他观察到当时企业家一经规模初成,便追求个人享受,以至于五六年或三四年便亏损倒闭,而“股东之本息,悉付之无何有之乡”,因此他强调“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 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在张謇身上得到继承和发展。据张謇自述,清末立宪时,由于“视察社会程度”相去甚远,于是不得不“兼注意于教育”。当时正值“纱厂营业日上,商承股东并竭私入,一意扩张小学,灌输人民必要之智识,与各实业分道并进,渐推渐广以迄于今”。他的志愿“不在专为股东营余利”,而在于“欲股东斥其余利之所积若干成,建设公共事业,为一国立些模范”。 因为“处智识竞争时代,民而愚,固不足言竞争,与语自治亦不可得”,而“不能自治,则乱之本”,后果必是“大可毙国,小亦毙乡”。因此,张謇颇重“教育普及”。他自称“一介寒儒”,之所以兴办实业,是“行吾所志”,而其志向便是如山东武训那样振兴教育。张謇称赞道,武训以一乞丐,一无所有,却“一意振兴教育,日积所乞之钱,竟能集成巨资,创立学塾数所”,此举可令“真士大夫对之而有愧色者也”。 在张謇看来,“实业、教育二事,有至密至亲之关系”。首先,“实业为教育之母”,因为“教育必资于经费,经费惟取诸实业”。其次,教育也不能脱离实业,张謇提倡“寓农工商于教育”。如在建立纺织学校时,张謇即解释了此举的目的:“工厂所在,设纺织专校,养成将来任事之才,工厂可容人见习,为甫营此业者,养成实事求是之助。”关于实业与教育的关系,他指出:“泰西人精研化学、机械学,而科学益以发明。其主一工厂之事也,则又必科学专家,而富有经验者,故能以工业发挥农产,而大张商战”,这就是“工业之发达,工学终效之征也”。当然“工学之构成,亦工业历试之绩”。由此,他倡导“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并寄望今日之学生“勉为有体有用之学,以副国家维新、选拔真才之用意”。 张謇所说的“教育普及”不仅指专门的实业学校,其教育蓝图是完整的,包括“普及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高等教育、武备教育”。他也重视儒家经典教育,只是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对其做了具体区分,认为《周易》《礼记》《论语》《孟子》当“哲学、教育学”,《尚书》“当历史、地理学”,《诗经》当“音乐、动植物学”,《春秋》三传“当法律、外交学”,《周礼》当“政治、经济、农工学”,《仪礼》《孝经》当“修身、伦理学”,《尔雅》当“国文学”,都是“专科而长于理想者”,此类专科须在“高等学校始得有之”。 “贫富相资,治安相共” 张謇不仅兴办实业,创办各类学校,也积极投身地方公益事业。他指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相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这是说,“既受教育,则宜有地方观念,对于地方公益、慈善、交通、水利诸要端,宜知其所以然,而爱护之扩充之,此受教育者应尽之责任”。可见,张謇也如传统士人,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担当意识。他指出:“须是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会;须是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人人肩上各自担起。肯理会,肯担任,自然不惮烦琐,不逞意气,成己成物,一以贯之。”关于慈善,张謇一直秉承“盖有实业地方,即应有慈善事业”的信念。 就创办养老院而言,张謇自言既不是“迷信者谓积阴功”,也不是“沽名者谓博虚誉”,而是基于“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得心安一点”。这无疑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恻隐之心。张謇还关注戏剧等通俗教育,认为“教育既求及于普通社会,而普通社会之人,职务余闲求消遣娱乐之地,多以剧场为趋的”,即“剧场实善恶观感之一动机”。此外,他还关心水利,对江苏境内的淮河、沂泗、运河等治理颇为关注,认为“我中华号称农国。水利者,农事之基”。1916年,张謇自称从事地方教育公益慈善之事十余年,育婴、养老先后建堂、立院,念“天之生人,最贫苦可闵者莫如残疾”,更设立残废院、盲哑学校。 就资本与劳工或者贫富关系而言,张謇对当时中国资本家的眼光短浅颇为不满,认为其“眼光尚未能辨科学之足以改进其事业”,只欢迎“人能包其事业赚钱”,而张謇认为欲赚钱必须仰仗“科学之精深,而须能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心理,量度社会经济,以为发展之标准”。他也指出,自己在办实业过程中感受到“资本家种种之势利”,几于罄竹难书,但并不能就此呼吁取消银行、股东等现代经济管理运行机构。张謇以股份制形式运营大生纱厂、盐垦公司等。他对“铲除资产阶级”等言行颇多批评:“凡百事业,动须资本;人之生活,全在勤劳”,而且“地方教育无已止之时,而个人担负有衰歇之日”,因此“非筹资产不能持久”。 就劳工与资本关系而言,张謇认可孙中山所说的“劳工、资本家利益在调和之说”,并以他个人经验,认为如果只抱定“志愿而不得资本家之辅助”,那么“二三十年来无一事可成,安有地方教育、慈善可说?”因此,张謇一方面认为“无资本家则劳力且无可谋生”,另一方面指出“无劳力人,资本家亦无可得利”,因此他希望“贫富相资,治安相共”;“从有益贫民着想始”,也必须“先使资本家安心投资始”。这是说,如真为贫民考虑,那么“当为之广设生计,若农之类,工之类,商之类,劳心之类,劳力之类,使有耳、有目、有手、有足之人,皆有所效以资其生;无耳、无目、无手、无足之人,亦有所安以恤其苦”,而“此资生恤苦之计”,都“赖资本为之”。 正是基于“贫富相资,治安相共”的观念,张謇高度赞赏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生为要”的观念,因为“唐虞三代皆君相为之擘画,而周特加详,其见于《周礼·地官》大司徒之职”以及“土地之图,土会、土宜、土均之法”均是民生之事;而且“于贫富丰凶之际,尤致意”,比如“保息六,三曰振穷,四曰恤贫,六曰安富;本俗六,五曰联朋友。正月布教,五家为比,使之相保”等。可见,其所以兴实业、办教育,其内心之志向便是恢复三代井田学校之制,其在南通所作实业和教育,正是“见圣人经训之不我欺”。因此,张謇认为《周礼》一书“调剂贫富之方法,粲然具备”,虽非社会主义,“颇足以泯除社会上之不平等”。 “立人之道,以义以仁” 正如张孝若所说:“我父是读书人,对于儒道的立论,认为十分的伟大精深,经孔子的推演,筑定了很坚固的根基,成了有系统的学理。他的伟大,是万事万物的原理,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总逃不出他的范围。”可以说,张謇一生对孔子、儒家的“仁义之道”是十分尊奉的。张謇认为孔子本“无宗教性质”,与佛教、道教为上等人说法“清净寂灭而失之于空”以及耶教、回教为下等人说法“洗礼膜拜而失之于固”均不同,孔子取“中庸主义,不偏不易,纯为人道”,是“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原无须凭借“国教而始重”。如果必以孔子为教主,则是“与佛道耶回争无谓之权,反觉小视孔子”。 但针对“自国体改革起,道德凌夷,纲纪废坠,士大夫寡廉鲜耻,惟以利禄膺心,一切经书,不复寓目,而诈伪诡谲之恶习,因是充塞于宇宙”的状况,他又极为痛心,而主张尊孔设会,呼吁“小学校即宜加授四书”,以使“儿童时代,即知崇仰孔道”。他发起尊孔会的意图就是“欲人人知人道之所在,而为有理性之人类”,具体就是“昌明孔学,宜就子臣弟友、忠信笃敬八字做起”,即“子为孝亲,臣为卫国,弟为敬长,友为爱人,此属于分际也;忠则不贰,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此属于行为也”。“人能明分际而谨行为,斯尽人道”,而“人道尽而后可以入圣贤之域”,这就是孔子“一身得力处”。 对张謇来说,“立人之道,以义以仁”无疑是其秉持的人生观、价值观。因为他同样认可传统儒者关于人之为人的规定,即认为“仁”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张謇指出:“人为三才之一,而万物之灵必具人之心而人乃成。人之心,仁是也。原一己之仁而施及人人,是之谓人之仁。”可见“儒者立身大本,曰智仁勇”无疑是张謇秉持的立身处世之道。他指出,所谓“儒之言”则“衣衣食食、居居处处、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朋朋友友、君君臣臣,范以礼而安于常,事至平淡而理极高深”,即“圣人之道则中焉”,而“中即事以为权,非执一以驭事”。 张謇指出:“圣贤经纶之业,无不从性分而来”,对君臣父子夫妇之“止仁止敬止孝止慈”之说颇为肯定,认为此是“合君臣父子而尽所为,止善之义见矣”。可以说,其所以兴办实业、振兴教育、从事公益也是从“性分”中来,正如杜恂诚所言,“大生纱厂和南通逐项事业的创办人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科举状元,此后投身于实业,“在价值取向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性”。 在兴实业与办教育的过程中,张謇极为重视道德与学术。他认为中国商业之所以一蹶不振,“可一言以蔽之曰不学无术”,并反思古代中国“取贱商主义”,而近年来虽然“渐渐崇尚实业”,但商界中“受教育者实少”,因此他组织了商业学校。其中就银行业而言,张謇认为“尤宜注重学术”,因为“银行事业,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对以前中国商人之道德,“素不讲求,信用堕落”的状况持批判态度。可见,张謇颇为重视商业与道德的关系,他指出:“商业无道德,则社会不能信用,虽有知识、技能,无所用之”。“知识、技能与道德相辅,必技能、知识、道德三者全”,而后“商人之资格具”。此处所谓“道德”便是“自我求之”,便是要求诸生在学校养成道德之习惯,即“毋谎言,毋占便宜,毋徒取虚名,著著从实上做起”。 张謇对“无道德之智识”也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无疑是“借寇兵齑盗粮”。也就是说,“无道德之智识”就如同把武器借给贼兵,把粮食送给盗匪。1915年,张謇批评晚近兴学之士“震惊于外人之物质文明,以为富强之基础皆在于是,而不悟彼之所以立国之本,用是道德一方”。如果弃置道德勿讲,只会造成“青年堕落,成材鲜睹,而浮夸之习,转以加甚”。因此,他倡导“待己,则以奋勉笃实为归;待人,则以仁民爱物为志”。他对学校教育中“修身”一项颇为重视,希望学生“既受父母干净之身,而仍以干净之身还诸父母”,指出:“对人宽,是之谓恕”,而修身之道“固多端”,不说谎不骗人即是一种。 对于士商关系,张謇认为:“商无士行者,驵侩数也。士不治生者,世大蠹也”,唯有“娴于商而士其行者,如是曰商,其殆庶也”。认可士商互通。简言之,张謇期待的是“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一个“良”字规定了农、工、商皆值得去从事,且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应该做好。这无疑是对传统耕读社会的更新,即把传统的关于儒学与农耕社会生活的融洽关联扩展为儒学与农、工、商诸种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容并处。 结语 2018年,资中筠指出:“中国在超过一个半世纪艰苦探索的现代化道路上,曾经出现过一大批实业家,对民族振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功不可没,却不大进入当代人的视野”。1927年以前实业家的代表人物是张謇,张謇之后有荣德生及荣氏家族(棉纺、面粉)、穆藕初(纺织)等,而且当时社会“中产阶层不仅是在经济实力上,更重要是文化意义上,主要由实业家和知识精英组成。他们承载了中西交汇的文化,大多数既继承了传统‘士’的特点,又是‘海归’,一起撑起了当时代表现代化的社会价值观”。正是这批实业家推动了近代中国新式工业、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但当下学界对这批实业家关注不多。关于这批实业家的研究不应仅限于探讨企业管理制度、企业文化、经营运作等问题,也应关注其“文化意义”,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传统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即其中“儒学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也许是最为常见的”。
文章分类:
学术研究-新时代张謇研究
|